文|胡栖安
古巴比伦王国君主汉谟拉比,与《史记》所载的商汤王居然是同一个人,你敢信吗?
近日,一篇2007年刊发于《武汉科技学院学报》的论文《〈汉谟拉比法典〉与商汤关系新论》引发关注。文章认为,“通过英汉两种语言的同源追溯,可以考证汉谟拉比在位期间所做的功绩,汉谟拉比本人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物能够跟《史记》所载的商汤王很好地吻合起来。”
好一个“吻合”,文章进而自豪地宣称,“由此,扑朔迷离的中华五帝史、夏史及商史,可以找到一条总的纲线。”作者的笔头稍稍偏一偏,中华的三皇五帝史,以及夏商周断代,就直接在遥远的美索不达米亚找到了传承有序的“正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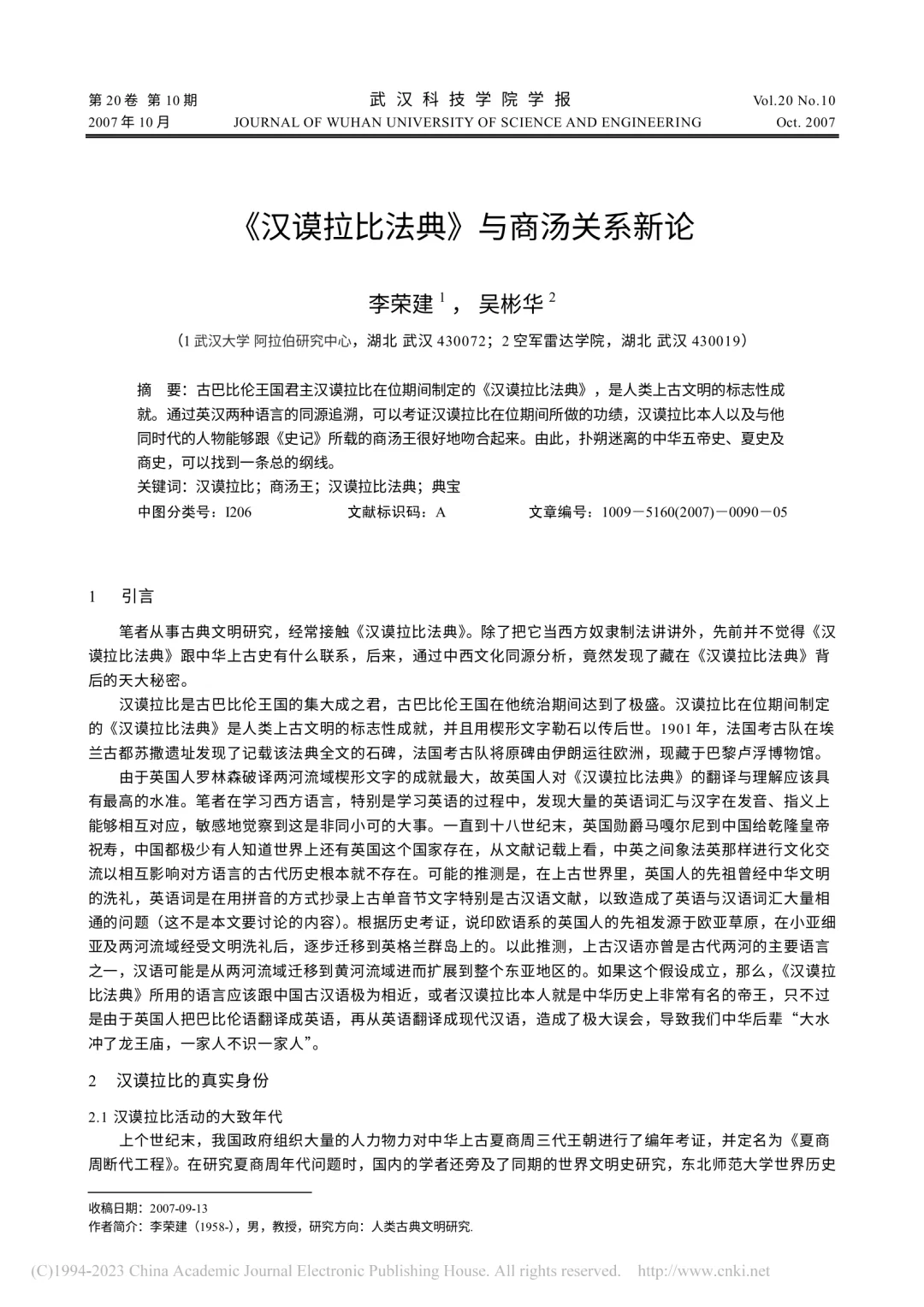
这样的颠覆性结论,尽管旁人听了很炸裂、很烧脑、很匪夷所思,但与之前湖南大学某教授提出的“英国人和英语起源于大湘西”相比,切近得多了,好歹还在一个大洲上,不用飘洋过海,陆路奔波,难度小得多。
然而,这一“勾连攀扯”,尽管地缘距离更近了,但思维的范式、认知的框架却并没有什么变化。依然是先入为主式的预设立场,依然是缺乏逻辑的各种猜测,依然是望文生义般的中英文对照……证据是什么,哪些事实可以支撑结论,似乎并不是作者所关心的。
这篇论文充斥着“推测”,而且还有建立在“推测”之上的“推测”。比如文中提到,“可能的推测是,在上古世界里,英国人的先祖曾经(接受)中华文明的洗礼,英语词是在用拼音的方式抄录上古单音节文字特别是古汉语文献,以致造成了英语与汉语词汇大量相通的问题。”
还有,“以此推测,上古汉语亦曾是古代两河的主要语言之一,汉语可能是从两河流域迁移到黄河流域进而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的。”“如果这个假设成立,那么,《汉谟拉比法典》所用的语言应该跟中国古汉语极为相近,或者汉谟拉比本人就是中华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帝王,只不过是由于英国人把巴比伦语翻译成英语,再从英语翻译成现代汉语,造成了极大误会。”
推论如此牵强附会,有人说,Ai都不敢这么编。
历史研究当然可以预设立场,但论证过程则必须严谨、扎实,不仅要有新理论的烛照,还要有考古学、社会学、语言学、自然科学等知识的支撑,任何一个阶段性的结论,都应该建立在基本事实之上。如此环环相扣,学术的基础才会扎实。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于17世纪末提出充足理由律,主张任何判断或命题必须具有充分且真实的依据,并强调理由与结论间的必然逻辑联系。若无视事实,忽略证据,只是想着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找到“一条总的纲线”,把两个古老文明强拉硬拽、叠加在一起,未免荒诞。
学术论文当然要有原创性,作者要有自己独到的见解,能提出新的观点、新的理论,因为科学的本性就是“革命的和非正统的”,但这种创造必须首先是科学的、符合逻辑的,不能胡乱猜测、编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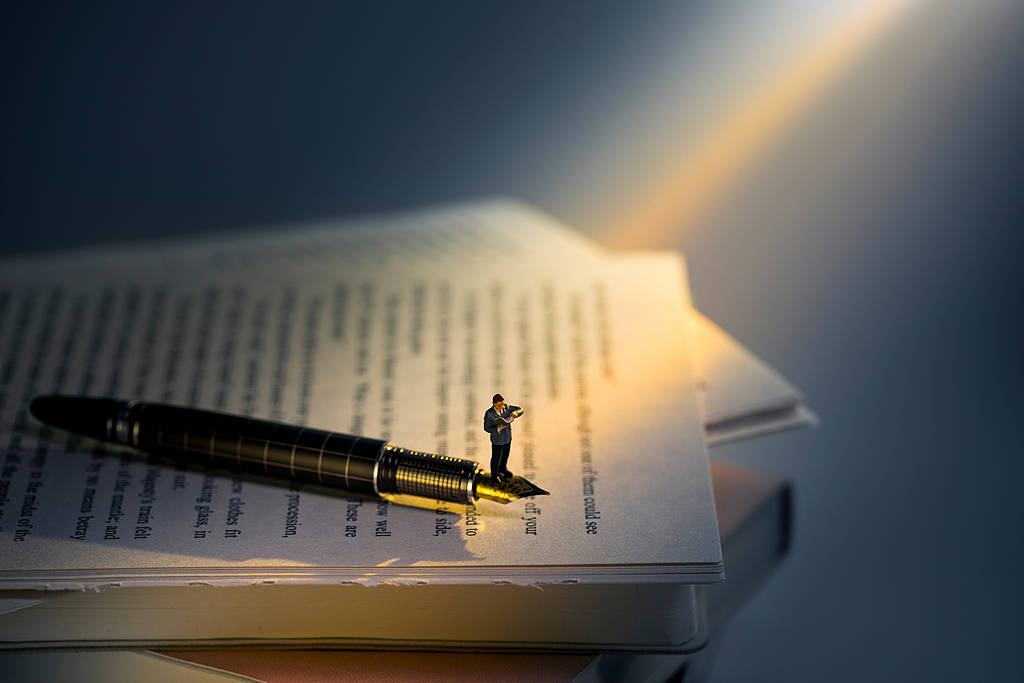
近年来,学术界时不时就刮过一阵一阵阴风。像“西方文明起源于中国”“英国人和英语起源于大湘西”,以及“汉谟拉比与商汤是同一人”等等,这些“理论”,貌似强调中华文化的深远影响、扩展中华文化的流布范围,实则更像是闹剧,既不能撼动西方史学,也不能改写中华史学。
倒是这个过程暴露出这些学者低幼的逻辑水平、拙劣的史学知识,以及丑恶的治学态度。学术研究可以各抒己见,但起码要在一个基本的水位线上讨论,不然,还要千百年来无数智慧头脑积累下来的知识做什么用?无视学术规则和常识,动辄就是超越,随便就能颠覆,这也太幼稚了。
《〈汉谟拉比法典〉与商汤关系新论》一文,两名作者李荣建、吴彬华均为高校专业人士,李荣建还是我国知名阿拉伯问题专家,曾以武汉大学教授、武汉大学阿拉伯研究中心主任等身份出席活动。不知该项研究是一时心血来潮,还是属于社科资助项目?
无论如何,作为学者,若罔顾基本的学术认知,缺乏基本的常识常理,以“学术研究”的名义,抛出耸人听闻的观点,是对学术界的伤害;身为公众人物,若利用自己影响力对大众认知形成干扰,也有误导大众,乃至有引起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嫌疑。
《武汉科技学院学报》并不是什么野鸡刊物,2010年更名为《武汉纺织大学学报》,是RCCSE中国核心学术期刊、湖北省优秀期刊。这不免让人纳闷,像这样的论文究竟是如何通过审核的?要在核心学术期刊发文并不容易,这篇文章又是如何脱颖而出的?
该文发表于2007年,时隔这么多年,再被网友扒出来、引发群嘲,对某些学者来说是一种提醒:文化溯源、文明溯源,是十分严肃的科学研究,真实永远是“总的纲线”;任何迎合某些群体、迎合某种想法的所谓“研究”,不可能被认可,也注定会成为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