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反做空一线
文/阳迪
2025年9月份,上海爆发绿捷学生餐事件,本次事件涉及50万学生健康这一重大公共利益,已引发社会公愤。然而深入研究之后发现,本次上海学生餐公共事件中,上海绿捷背后股东是刘永好的新希望集团及刘氏家族,其通过离岸信托牢牢掌控了上海绿捷的100%股权,这让金融界人士长期畅谈的离岸信托与控制权责任问题,一下子成了焦点和核心问题。

图源:时代周报
媒体报道已清晰勾勒出“资本逐利→压缩成本→食品安全失控”的链条,而本案件的核心在于:绿捷实际控制人的离岸信托能否让最终受益人完全隔离于所有类型的风险,尤其是在涉及公共利益、食品安全等重大法律与道德责任的领域。
而近期香港高等法院的一项判决,可能对一些意欲通过信托资产避债的行为形成实质性的障碍,同时也让国内富豪阶层对“海外信托永不灭失”的迷信破产,为跨境追赃树立里程碑式先例。
上海绿捷被刘永好家族牢牢控制
根据公开信息,刘永好家族对上海绿捷的控制关系路径如下:
刘永好家族通过其离岸家族信托(Ananta信托) 持有澳大利亚公司 Kilcoy Global Foods (KGF) 45.44%的股份,为第一大股东。厚生资本(与新希望集团关联紧密)持股38.95%,为第二大股东。
KGF通过一系列设在开曼、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和香港的子公司(KGF Asia Holding, Ltd → GreenExpress Foods (BVI), Ltd → GreenExpress Foods, Limited),最终100%控股上海绿捷。
KGF的董事会中,刘永好之女刘畅、新希望集团副董事长王航等核心人物位列其中。
上海绿捷现任董事长陶煦也与新希望系有密切关联。陶煦担任新希望全资子公司"金橡树投资控股(天津)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上海绿捷的股东为香港公司 GreenExpress Foods, Limited,其董事王航是厚生投资的创始合伙人。而厚生投资的第二大股东,经股权穿透后,最终实际控制人为刘永好(新希望集团创始人)。刘永好家族通过股权和人士安排,形成了对上海绿捷形成了“资本+人事”的双重控制。
因此,刘氏家族的确通过离岸信托→离岸公司→香港公司的多层嵌套结构,实现了对上海绿捷的最终控制,这也是华尔街金融炼金术“循环控股”的一个生动案例。
这样的多层嵌套的法律结构,表面上刘永好家族可以“只享受收益,不承担法律风险”。由于信托的核心功能是风险隔离,但非绝对“保护”。离岸信托和离岸公司架构在法律上确实构成了责任防火墙。
在本次学生餐事件中,如果仅追究直接的行政或刑事责任,如食品安全法对应的处罚,那么执法部门通常会直接处理上海绿捷及其直接负责的人员,如本次被立案调查的实际控制人张某某、总经理董某某。从这个层面看,躲在架构顶端的刘氏家族成员个人直接承担境内刑责或行政责任的风险较低。
但信托并非“免责金牌”,基于以上许家印案的宣判,上海绿捷存在被“穿透”的可能,在以下情况下,离岸架构的防火墙可能失效:
基于“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如果法院认为离岸信托只是虚假外壳,委托人仍对信托资产进行实质控制,则可能“击穿”信托,认定资产仍属于委托人。张兰案就是因此被击穿信托的典型案例;另外,用于非法目的,即如果设立信托的目的是为了欺诈、逃避债务或进行违法活动,该信托同样无法提供保护。
有法律界人士认为:虽然刘永好家族可能暂时避免了直接的法律制裁,但刘氏家族及其商业帝国依然面临着其它严峻的风险,这些风险同样具有巨大杀伤力。
许家印信托被香港高等法院判决穿透
2025年9月16日,香港高等法院作出一项史无前例的裁决:对恒大集团创始人许家印名下77亿美元的全球资产实施接管,并首次明确将其离岸信托资产纳入接管范围。
外界评价认为,这一判决不仅标志着恒大债务危机从公司清盘走向个人追责,更以“穿透信托”之槌,击碎了国内富豪阶层对“海外信托永不灭失”的迷信,为跨境追赃树立里程碑式先例。
事实上,按照法律界人士的看法,香港高等法院此次的裁决,核心在于运用“实质重于形式”原则,穿透了许家印离岸信托的法律外壳。
这并非否定信托制度本身,而是针对其滥用行为。穿透的依据主要来自两方面:最根本原因来说信托成立意图涉嫌欺诈债权人,法院裁定的法律基石是“欺诈性转移”原则:即任何旨在损害、延迟或欺骗现有或潜在债权人的资产转移行为均属无效;另外,关键在于资产注入信托的时间点上来说,如果委托人在转移资产时已经资不抵债,或此举导致其无力偿还已知债务,则该行为被视为具有欺诈意图。
进一步来说,香港高等法院认定,许家印在恒大危机爆发期间将资产转入信托,主观上明知公司债务危机即将爆发,其目的是在债务“雪崩”前转移资产,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

图源:凤凰网财经
此外,许家印与丁玉梅的“技术性离婚”及资产转移安排,与信托计划被法院认为是同一套“资产保护策略”的不同步骤,这一认定极大地强化了“欺诈意图”的证据链。
从直接原因来说,委托人对信托财产控制过度,法院在审查中发现,许家印作为委托人,可能过度保留了控制权。尽管信托契约的具体条款未公开,但此类架构通常允许委托人保留过多权力(如投资决策权、撤销权、变更受益人等)。如果委托人实际上仍能像控制个人银行账户一样控制信托资产,那么法院很可能认定该信托是“虚假信托”或“委托人的延伸”。在这种情况下,信托在法律上不具备真正的独立性,其资产被视为委托人的事实资产,必须用于清偿其债务。
许家印并非海外信托被击穿的首个案例。“俏江南”创始人张兰的海外家族信托早在2023年就被新加坡法院击穿,原因与许家印案惊人地相似。张兰过度保留控制权——她被认为对信托财产享有实际控制权,可以任意取回和处分。被认定为“虚假信托”的原因:法院认为,张兰在设立信托后,仍将信托资产视为自己的个人财产随意调度,这使得信托的“独立性”名存实亡。
张兰和许家印的案例共同表明,在普通法系下,法院更关注交易的经济实质而非法律形式。离岸地提供的强大保护,并不能对抗委托人的欺诈行为和过度控制。
判决对财富管理行业具有颠覆性
许家印案的判决,为所有关注财富保护与传承的人士提供了颠覆性的启示:
信托是“盾”而非“矛”。信托是守护合法财富的盾牌,绝不能作为掩盖非法所得或逃避合法债务的“避风港”。试图用它来隐匿赃款、对抗债权人,本质上是将法律赋予的防护盾,当作了攻击性的矛来使用。
合法性是唯一基石。财富来源的合法性是任何信托结构得以稳固的绝对前提。用非法财产设立的信托自始无效。在刑事司法实践中,一旦信托资金被查明涉及犯罪所得,无论其法律形态如何转化,均可能被作为“赃款赃物”追缴。
“控制”与“隔离”难以两全。追求对信托资产的绝对控制权与实现资产隔离保护之间,存在天然的内在冲突。委托人对信托的干预越多,其“独立性”就越脆弱,被击穿的风险也越高。
跨境追赃能力已今非昔比。此次香港法院的判决,并与英国等法院联动,许家印前妻丁玉梅已经被发出全球禁制令,清晰地展示了中国司法机构与普通法地区在跨境追索方面的有效协作。试图通过复杂的离岸架构藏匿资产以逃避法律责任的难度已急剧增加。
这一标志性事件预计也将深刻影响未来的财富管理行业。市场将告别对离岸信托的盲目迷信,转而更加依赖专业人士(律师、税务师、信托顾问)提供的合规设计与实质性规划;财富管理的核心逻辑将从“如何隐藏和保护”,回归到“如何合法、合规地创造和传承”。真正的安全根植于财富本身的清白与业务的正当性。
总而言之,许家印案例的深远意义在于,它撕碎了那些试图利用法律工具进行财技游戏的伪装。它郑重宣告:法律保护的是诚信与合法的财富秩序,而非处心积虑的规避。 真正的、坚不可摧的“避风港”,唯有财富的合法性与经营的正道。
法律将更注重实质正义
目前,上海绿捷已被临时接管,其垄断上海校园餐市场的业务模式难以为继。上海绿捷的母公司KGF正在冲刺美股上市。此次事件无疑给其上市之路蒙上浓重阴影,甚至可能导致上市计划搁浅。
虽然刘永好家族个人直接刑责风险小,但如此重大的公共事件,调查机构不可能不深入研究资本方在成本控制、利润指标设定上是否存在系统性过错。如果查出资本方明知并纵容甚至要求以牺牲食品安全来换取利润,则不排除法律调查向更深层次延伸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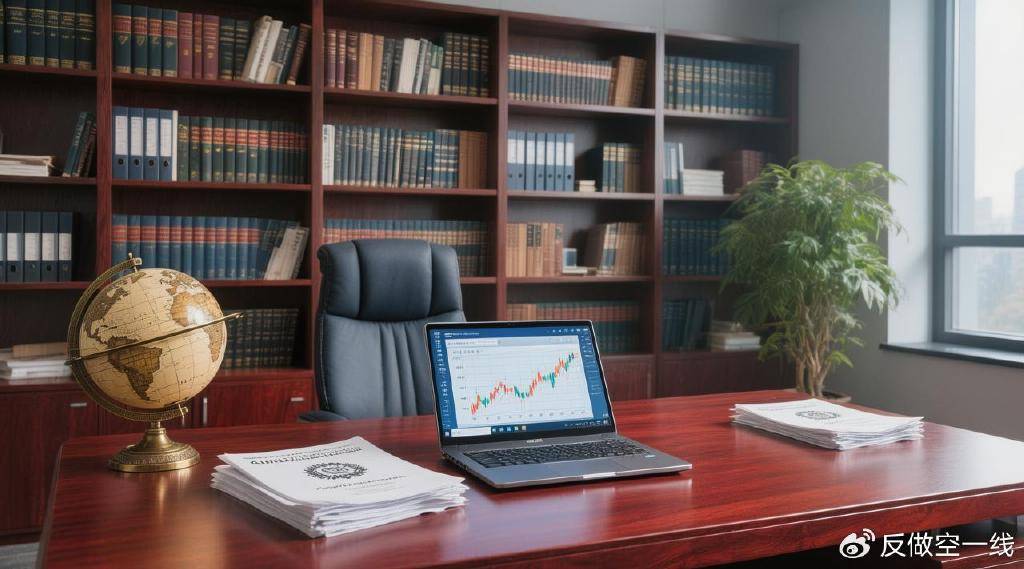
图源:AI
总的来说,认为离岸信托能让最终受益人“只享收益,不担风险”的看法是片面的。在法律技术上,它确实设置了一道责任防火墙,尤其在隔离直接个人责任方面,产生了一定积极的作用。
然而,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事件面前,从目前许家印案例的宣判来看,法律正在走向“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强大的声誉风险和市场反噬力量,将会形成一种更强大的“穿透力”,这将成为中国法律面对信托架构后的重要走向,不管是普通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精密的资本架构可以隔离部分法律风险,但无法隔绝道德责任和公众的审视。
许家印案的裁决与上海绿捷案的查处,共同彰显了一种清晰的趋势:法律正在更加注重 “实质正义”。对于企业的实际控制人而言,这意味着必须为其决策和行为产生的所有后果承担起最终且无法推卸的责任,无论是金融债务还是公共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