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关心】
年仅19岁的大学生刘某某在南昌景区游玩时惨遭杀害,令人痛惜,但警方通报中关于行凶者席某某有“精神疾病诊疗史”的信息,更让人心塞。行凶者会不会因此逃避死刑甚至刑责,是人们最关心的问题。
有网友担心,警方通报中的“精神疾病诊疗史”信息,是不是为将来的从轻或免除刑责做铺垫。需要说,这种担心是没有必要的,这只是一个事实陈述,可能与案情有关,因此通报满足大众知情权,但不会影响最终的判决,更不意味着他可以逃过一死。
我国《刑法》第十八条已构建了精神病人犯罪三级责任框架:完全丧失能力者免责但需强制医疗;间歇性患者正常时犯罪担全责;部分丧失能力者需担责但可从轻。这清楚地表明,精神病人并不等于免罪免罚。我国刑事立法明确采取医学标准与法学标准相结合的混合标准认定精神病人的责任能力:既要依据医学诊断——罹患精神疾病,同时又要参考法学标准——丧失了辨认或控制能力,才能够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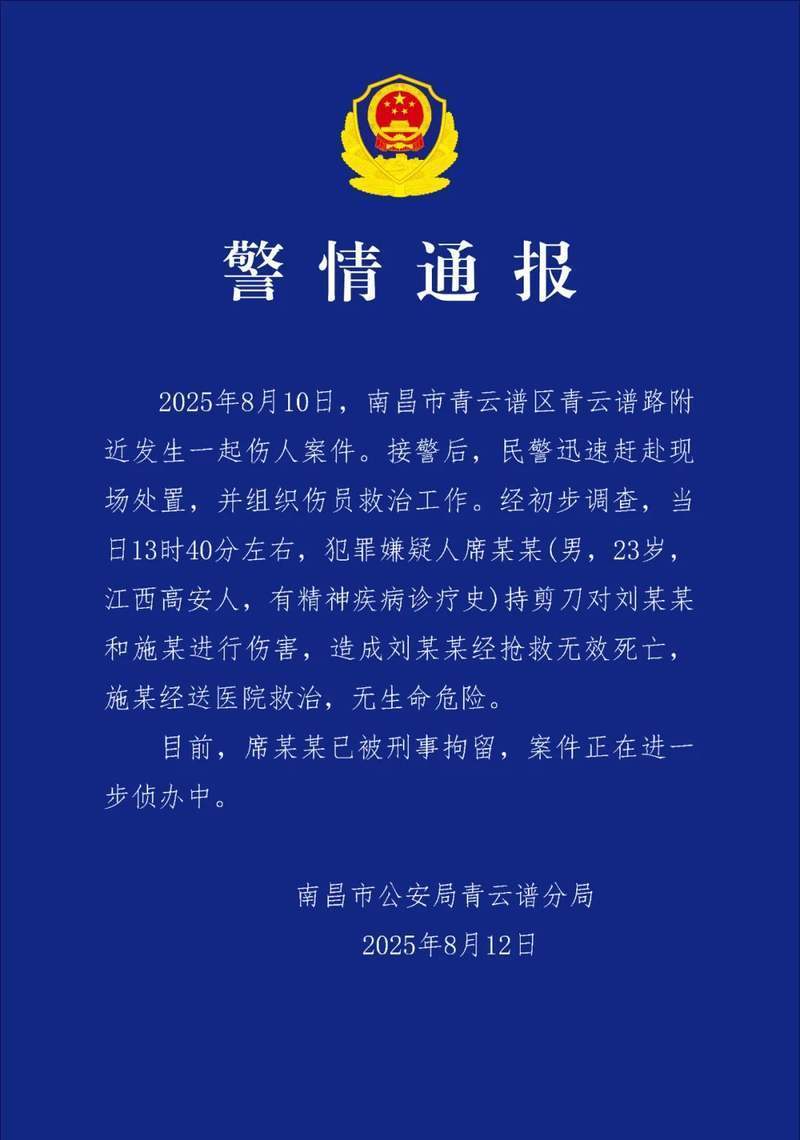
“8·10南昌景区女大学生被男子捅伤致死事件”警情通报
本案可参照2020年的李某锋搭讪遭拒刺死女大学生案,尽管李某锋主张“醉酒精神分裂症”,但因鉴定显示作案时精神正常,最终被判处死刑。本案席某某同样因为搭讪遭拒而行凶,犯罪行为是有逻辑的。仅凭病史记录,并不自然产生“免责”的结果,其中需要经历大量的医学和司法程序。由于本案受到舆论的高度关注,该程序必须经得起最严格的检验。
一方面,当前精神疾病诊疗领域存在隐患:诊断标准的主观性和不统一、鉴定机构水平的参差、诊疗记录真实性的存疑,为责任认定埋下不确定性。实践中,“临时性精神病”、“间歇性发作”等模糊概念常被滥用,甚至滋生“花钱买证明”的灰色产业链。这种医学层面的不严谨,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法律执行的公信力。
另一方面,法律的执行存在难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关于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判断尚无标准,基本依赖相关司法人员的主观经验和认识,也取决于能否对事件发生经过进行真实、细致的还原。同一案例,在不同鉴定机构进行评定时未必意见一致,初鉴与重新鉴定的结论也未必一致。所以,经常有控辩双方申请重新鉴定的情况;而最终是否采纳,需要法官结合所有的证据材料,进行综合判断,这当中又存在一定的主观因素。
公众对恶性犯罪“从轻处罚”的天然抵触,极易引发对司法公正的质疑。从目前公开的信息来看,南昌案的嫌疑人针对完全无辜的陌生学生施以极端暴力,持剪刀连续捅刺,手段凶残且目标明确。其行为模式展现出的目的性与控制力,很难说符合“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的法定免责标准。若因其“精神病史”获得从轻甚至免罚,不仅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可能加剧公众对法律漏洞的担忧,甚至引发对真正的精神疾病患者群体的误解与歧视。
中国人常常有一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这是朴素而基本的正义观,本案审理时也应有这方面的权衡。这种情绪,既是对无辜生命骤逝的朴素愤慨,更是对法律守护社会最基本安全底线的强烈诉求,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